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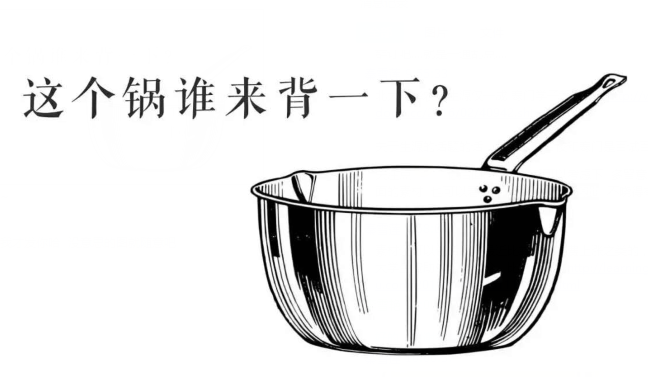
学生说,我们爱学习,但我们不爱去上课。老师说,我们喜欢教师的职业,但我们不爱讲课。如此矛盾的表述背后,是大学好课无几的尴尬。到底哪里出了错?
教师为“好课寥寥”喊冤
2016年5月,《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篇《大学“好课寥寥”》引发了高校教师热议。文章中指出不少大学老师讲课的问题:“老师几个学期开同一门课,PPT常年不换,照本宣科地朗读,没有太多板书,所出的试题甚至经常照搬往年原题。”
对于这个问题,学生感同身受。他们抱怨老师讲课枯燥无味,一些教师授课水平还不如中学老师,却不满于学生上课玩手机、聊微信。有学生直言“我们努力了那么多年,不是来听你念PPT的”。甚至有人提问:“学生能就大学教师教学质量低下诉诸消费者协会吗?”
当学生异口同声地讨伐课堂教学质量不佳时,很多教师则表示出无奈和苦衷,他们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可是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在众多评论中,当前高校“重科研轻教学”是教师讨论声音的焦点,其核心就是教师考核绩效。科研成果能为评职称和年终考核加分,教学效果却看不见摸不着,能量化的只有时间,将讲课时数填在年终总结里而已。当二者难以兼顾时,教学好的老师可能科研不太强,科研强的老师有些真讲起了课又不太像回事儿——这一情况就在所难免。《中国青年报》的官方微信账号下面,一位高校教师看罢此文评论道:“搞科研的(教师)较少深入社会生活,讲课照本宣科,就不新颖生动、脱离实际。经常参与社会活动的(教师)又不能静心钻研教学,讲课敷衍了事、心猿意马。这两种教师都是学生不喜欢的,不愿听他们的课。”评论获得45个赞,显然一些读者颇为认同其观点。
在教学质量不佳的背后,还有好老师不上课的尴尬情况。大一大二的通识课、基础课的主讲人往往是博士毕业不久的大学“青椒”或兼职教师,教学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教授们往往只负责科研和带硕士、博士生,不少学生大呼,直到本科毕业都没有见过院系网站上宣传的学术名家泰斗们给自己上过一门课。如此的漏斗形师资分布也是好课寥寥的原因之一。
一篇文章引发了高等教育界对“好课寥寥”问题的大讨论,可是问过“为什么”之后,讨论过后,无论是文章中还是高教内部,都未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法。难道大学“好课寥寥”现象真的无解吗?
把教学型教师“捧上天”
科研和教学难以兼顾,这是许多大学老师的痛点。教学无法成为职业晋升的通路,科研却能辅助职称评定,放弃教学抓科研就成为人之常情的选择。在这种情形下,专注教学似乎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执着。但在国外,以教学为重的老师也能有“春天”。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以下简称UBC)早在20年前就建立了教学型教师晋升和终身教职评定系统。讲师在工作5年后可以申请教学类终身教职,还可申请职位晋升为高级讲师。不过高级讲师的级别相当于研究型教师级别中的副教授,也就是说“副教授”成为教学型教师职业晋升的天花板,彼时,专注教学无法让UBC的教师获得正教授头衔。为了表示对教学的重视,2011年7月,UBC设置了“教学教授”的级别,并正式发布了教学教授晋升指南。
2012年首次评选,物理天文系教师西蒙·贝茨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得教授席位的4 名教师之一。如今,贝茨是UBC教学学习与技术中心主任和教务处的高级顾问,在担任行政职务百忙之中还在物理天文系教授一门物理学入门课程。
到2016年,获得教授一职的教师已达20人。UBC人力资源部门表示,设置教学教授这一级别主要是为了起到树立榜样的作用,是目前教学型教师能在UBC 获得的最高荣誉。教学型教师在被评为高级讲师的第五年即可申请。
教学教授评定主要考察四方面:
●教育领导力(指导同辈教师、学生,在系内、学校内担任领导职务等)
●教学(教学任务完成度、学生和同行评教结果)
●课程开发和教学法创新
●服务(在系内、学校和社区参与学术服务,比如加入委员会、提供指导等)
国外高校对于教学型教师的支持为其职业道路选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教学型教师也不再比科研型教师“矮一头”。心理与神经系统科学系教师詹妮弗·斯坦普在2000年来到加拿大戴尔豪西大学任博士后一职。2003年,校方邀请她正式加入教师队伍。从那之后,她专注教学领域,级别逐渐提升,先是获得了终身教职,然后拿到高级讲师职位。2015年12月,她拿到了校方新设立的“教学研究员”一职——教学型岗位最高级别。斯坦普是剑桥大学的博士,许多人曾跟她讲,选择教学意味着浪费自己的剑桥博士头衔。但出于对教学的热爱,她一直在这条路上坚持了十多年。十多年间,她写了自己的教科书,当过本科部主任,带领本系进行网络课程开发,学生在评价中对她不吝溢美之词,是当之无愧的名师。一般情况下,她的教学任务是每学年八门课,其中包括一门1000人的大一基础心理课程。教学型教师并不是不能搞科研。在本系的支持下,她还进行了关于压力和上瘾问题的小范围研究。
目前国内高校对教学型教师主要采取奖励的方式。比如浙江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设立教学奖金,部分单项奖金高达100万元人民币。评选方法通常结合学生评教、院系教学业绩考核和在线投票等多种方式,以给专注教学的老师更多尊重和认可。
对不上课的教师说“不”
对重视教学的教师予以级别晋升和奖励,如果教师忽视教学,学校要如何处理呢?2015年,美国密苏里州参议员柯特·谢弗向密苏里大学系统“开炮”,矛头指向该大学系统内的一所分校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因为根据一份备忘录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里,该校超过1/3的终身教职教师没有达到学校的最低授课量。
谢弗表示:“如果这一数据说的是橄榄球教练,那他们铁定会被开除。(教师教学的)数据这么触目惊心,高校如何期待经费会增长呢?”他认为高校需要内部自查,未来检查教师教学量是否达标应成为评定高校是否完成改进目标的依据之一。因为教师未完成基础教学量,密苏里州打算不通过此前商议的为州内公立院校增加6%预算的议案。
最低教学量是怎么回事?很多美国院校为约束教师,防止“重科研、轻教学”问题发生,都会对授课量做要求。以美国波士顿大学为例,同样是研究型大学,该校文学与科学学院要求教师每年至少上四门课,这一要求与全美范围内的研究型大学文学与科学学院要求保持一致,但其不同院系和专业对教师承担课程量要求存在一定差异,比如自然科学的教师年承担的课程量大约为2~3门,因为该领域科研更多。课程数量是对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考核之一,但班级规模越大,工作量也会相应增加,所以课程人数也会被考虑进来。原则上说,只要所在系内设有本科项目,所有教师都要每年讲授本科课程。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学院可以适当降低对研究型教师的授课量要求。但当研究并未处在关键阶段时,授课量不予降低。对于已经获得终身教职、在科研基金和研究方面不再活跃的教师群体,院方还会将授课量要求提高。
上海市教委从2014年秋季开始推行上海市属本科高校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明确提出凡受聘教授、副教授岗位的教师每学年为全日制本科学生的授课,不得低于108个课时;担任行政或其他职务的“双肩挑”教师,不得低于54个课时;每学年均需承担指导青年教师、培养助教或博士后任务,教授带教人数不少于2人,副教授带教人数不少于1人。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表示:“博士刚毕业,还不具备教学经验的新教师马上给本科生上课,而教授们则往往忙于科研。现在要做的,是把教授的‘人’和‘心’都拉回课堂上来。”
新闻链接
近期,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教授、副教授(高级职称教师)更多承担本科教学任务,并将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授聘任的基本条件。(教育部网站,2016-07-04)
教学是大学核心理念的基础层面,也是教师最基本的任务。一位大学教师在知乎上说:“只要有一个人听(课),我就必须好好讲,用心讲。做好自己的工作,问心无愧。”教师对责任的坚守、高校对教学的重视,这或许能够成为扭转“好课寥寥”状况的关键。